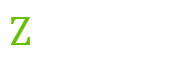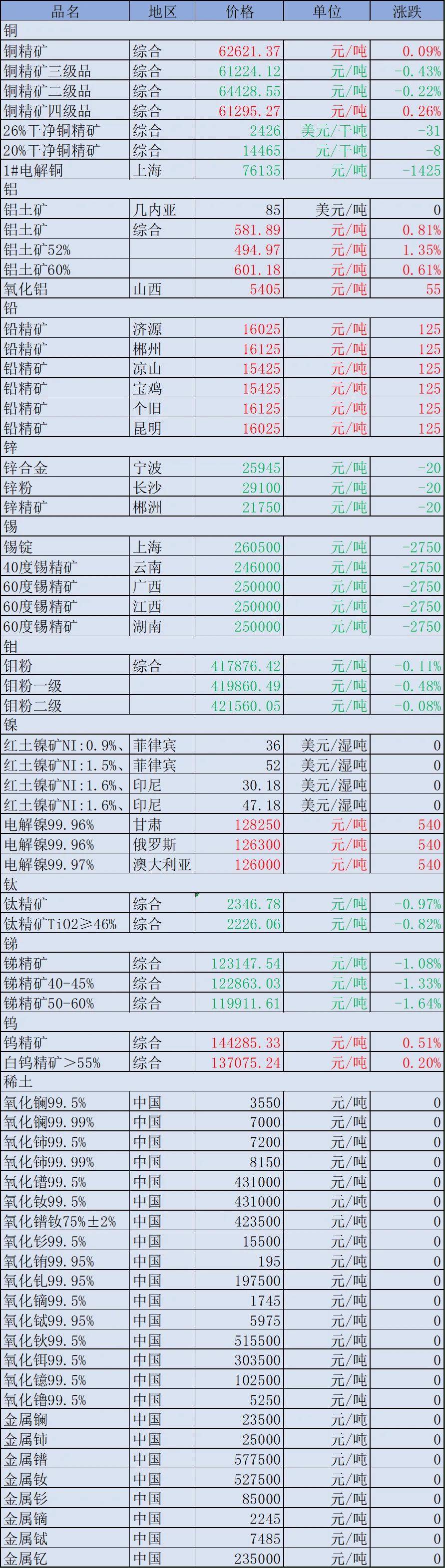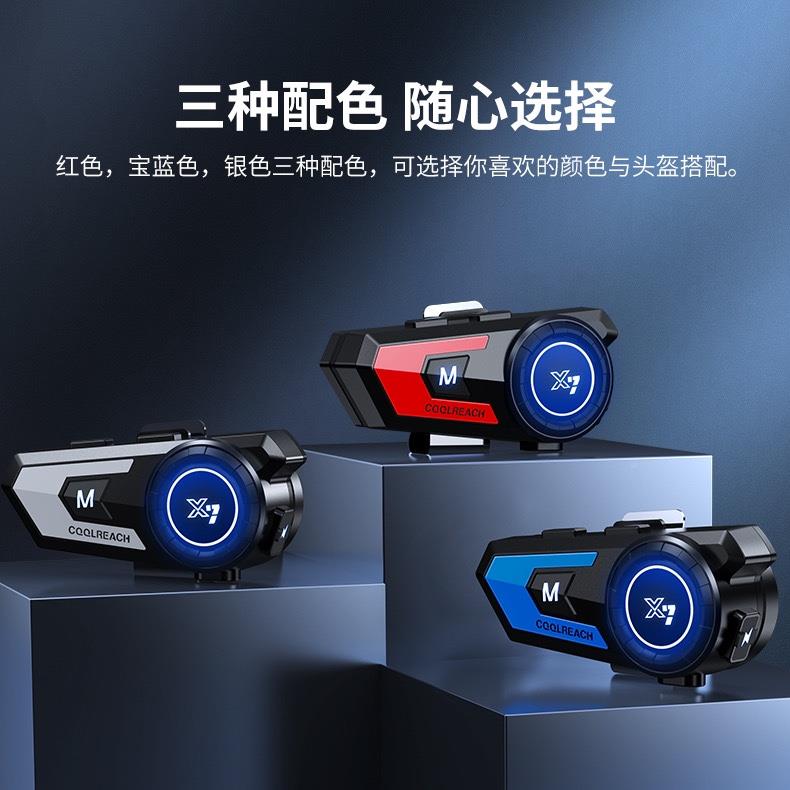我出生于1970年,小时候住红桥。小时候去幸福大街无外乎三件事:跟大人去幸福商场买东西;去工人俱乐部看电影;到邻居王叔叔的单位去玩。
1990年,我职高毕业被分配到天坛饭店工作,天坛饭店就在幸福大街的南口路西,从此和幸福大街又有了近三十年的相伴。
很早就想写幸福大街了,但苦于不知从何下笔。最近我也几次徜徉在这条熟悉的街上找灵感,还是不得要领,我也是真是没招儿了,那我这回就写个流水账吧,我们把思绪带回到二十多年前。
刚才说过了,天坛饭店就在幸福大街南口路西,幸福大街在这里与体育馆路相交。以前这儿有个玉清观,后来叫玉清胡同。饭店于1990年开业,在盖饭店时工地上出过一件大事——亚硝酸盐中毒。出事那天我还间接亲身经历了,话说这事儿发生在1987年左右,我家已经搬到体育馆西路。
那天我是骑车去首体买演唱会的门票,出家门就老有救护车和我对脸儿而过,救护车不是一般的多,多得让我心里有点儿发毛。
晚上回家看《北京新闻》,才知道天坛饭店工地出事儿了,工地的厨师误用工业用盐给工人们做饭,引发了亚硝酸盐中毒,那会儿北京市市长是陈昊苏(陈毅之子)。
好多老同事都说让我写写天坛饭店的今昔,那可是个大工程,待以后有能力吧。
书归正传,幸福大街呈南北走向,长度约一公里。天坛饭店奔北以前是水暖器材一厂,在水暖厂门口还有个门市部,我当年还在这里买过马桶盖儿,以前所说的马桶盖儿和今天说的可是两个概念。
后来水暖厂这块儿地进行了房地产开发,现在的楼盘叫天坛公馆,属于僻而不偏之地、每平米的均价已经超过了十万元。我有朋友住里面,光凭着一套房子他就是千万富翁。
从水暖厂再奔北是一溜饭馆,有一家饭馆我印象最深,因为这家饭馆里有棵树,就是和电视剧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里张大民家一样。我和同事经常光顾这家饭馆,虽没啥特色,但饭菜比较便宜。再往北是个部队的院子,这块儿还有一家叫做豪门啤酒城(或叫酒楼)的大饭馆,这里消费比较高,几乎没去过。
这一溜饭馆断断续续到文章胡同东口,把着文章胡同口的是一家新疆饭馆,这饭馆是个里外间儿。有一次我和同事在这吃饭,还和饭馆老板产生了摩擦。那次我们发现烤熟的羊肉串颜色不对,我们就招呼老板过来,其实我们也不能断定是不是羊肉的问题,说实话叫老板过来只不过是想让老板把这串换掉,然后再送个小菜或啤酒啥的。
这老板铁嘴钢牙,并且信誓旦旦说羊肉没问题,我们说要是这样就给防疫站(现在叫疾控)打电话投诉,老板并无胆怯之意,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我们觉得他这样淡定应该是羊肉没事儿,也是嫌麻烦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说着说着就到了文章胡同,文章胡同东西走向。旧时道教庙文昌宫在此地,所以此胡同称文昌宫,后来依“文昌”的谐音,就叫文章胡同了。
从文章胡同奔西就是南岗子、北岗子了。这里在旧时就是乱坟岗子,有图有真相,各位!现在文章胡同47号院门东侧还残存一块石碑,石碑被砌到墙里才被保留,石碑上刻有“浙绍新义园”的字样。义园就是义冢地,丛葬之所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益性墓地。
再奔西就是营房和法华寺街了,我小学就在法华寺街小学念书,那会儿校园内只要一挖坑,总会挖到人骨头,有时还能挖个骷髅来,同学们都见怪不怪了。
那会儿我们这片儿有一个顺口溜儿:一小(法华寺街小学)是坟头,二小(法华寺旧址也曾是小学)是破庙,三小(据说指营房小学)是个好学校。
想当初,我小时候南岗子最有名的是一家馒头铺,每当过春节的时候姥姥都会让我去买大量的馒头。
出文章胡同,幸福大街上继续再往北,街面上以民房居多,四十九中的东门就开在幸福大街上,学校合并后,现在是一零九中。
幸福大街再向北稍稍地拐了个弯儿,这里有一座幸福大街上的大工厂——北京六零八厂。大家都知道,一般凡是工厂名以数字表示的都是高精尖保密单位或军工企业。北京六零八厂主要从事光学玻璃制造,好多朋友会对这个工厂比较陌生,那么提到博士伦隐形眼镜大家会熟悉吧,博士伦就是1987年该厂和美国博士伦合作生产经营的产品。
1976年,咱国家净出大事儿。六零八厂承担了毛主席水晶棺及棺内照明系统的全部设计及制作。
现在六零八厂的后院有《新京报》社常驻于此。和《新京报》的接触是近些年的事儿了,因为我喜欢摄影,后经常登录《新京报》的拍者网,拍者网会不定期的举办摄影讲座。
六零八厂往北行,没多远就到了十字路口,十字路口正西是半壁街,西南是永生巷。永生巷里有家工厂,厂名大家也许不熟悉,但产品很多朋友都用过。这就是北京三露厂,大宝牌系列化妆品大家都知道吧,就这儿生产的。现在的三露厂搬亦庄去了。
想必此时此刻大家耳边都会响起“大宝,明天见!”、“大宝,天天见!”、“要想皮肤好,早晚用大宝”等广告语吧。顺便说一句,三露厂是福利工厂,工厂里残障人士比较多,以前经常在幸福大街看见残障人士结伴而行。
从三露厂出来沿永生巷再往西,南岗子天主教堂屹立于此,该教堂已建成100多年了。在北京说起天主教堂,一般都会想到东西南北四大堂,东堂——王府井、西堂——西直门内、北堂——西什库、南堂——宣武门。这南岗子堂深藏于老旧平房之中,每年的平安夜都会举办活动。
咱们还是回到幸福大街,再往北就不说了,北边有几家小商店,去的也比较少。幸福大街的北口与两广路相交。
我们过马路,来到了幸福大街的马路东边,东西走向的培新街就在眼前。培新街地名的由来据说和这条街上的学校扎堆儿有关,这里先后有二十六中(现恢复旧名叫汇文中学)、北京小学、培新小学在此地搬迁或落成。
我上小学的时候,二十六中是南城赫赫有名的好学校,她最早叫汇文中学,由崇文门搬迁而来,后来又恢复了老的校名。
在那会儿谁家孩子要是考上了二十六中就和中了状元一样。我小学同班李同学,因腮边有块儿胎记,并且胎记上长毛,所以同学一下给他起了两个外号,其一叫“一撮毛儿”,其二叫“台湾岛”,为啥叫“台湾岛”呢,因为他的胎记的轮廓特像台湾地图。
李同学从上学的第一天就学习成绩优异,我那会儿感觉他就不是人……就是个神,现在管这种人叫学霸。李同学能上二十六中大家都觉得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
结果他小升初考砸了,和我一起考入了十一中,班里平时学习也不错,但不是特优秀的杨同学考上了二十六中。但金子总是要发光的,后来李同学考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。这一说和李同学也快30年没见了,李同学,你还好吗?公开你的外号别生气啊,如果能看到此文章请联系我。
培新街上的崇文小学也值得说说。崇文小学建校于1960年,为寄宿制学校,主要接受华侨、专家、外交人员的子女及少量外籍学生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曾被“公派”去过一次,我那会儿是学校鼓号队的(说是鼓号队,其实已没有吹号的),我司职小镲。有一年崇文小学举办活动,我们鼓号队去助演,当天我们穿着整齐的服装从法华寺街小学出发,边走边敲,引得附近街坊都上街驻足观看。到了崇文小学,用现如今的话说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,人家举办活动在礼堂里,甭说那会儿,就说现在,也没有几个小学有礼堂。
现在崇文小学搬到花市枣苑去了,她的原校址已被汇文中学占用。前几天去了趟培新街,汇文中学的老楼正在修缮之中。对了!那会儿还有说这教学楼是用建人民大会堂的剩料盖的,不知是真的假的!
培新街上还有崇文儿童医院,小时候来过这里看过病,但次数不多,妈妈更爱带我去第四医院(普仁医院),后来改去同仁了,看病的故事我以前讲过。
车务科以前也在培新街,后来搬走了,原地盖起了培新宾馆,再后来培新宾馆歇业了,现在大楼没有挂牌,好像也是一处办公的地方。
幸福大街集中了区级党政机关。从培新街出来奔南,这可来到了崇文区的“心脏”。首先是崇文区图书馆,图书馆是一座五、六层的白楼,我在当时还办过图书馆的阅览证。图书馆的楼上还有百花(歌)舞厅,这地方当时吸引比较时尚的青年,我们饭店中餐厅的几个漂亮女服务员就常去。
现图书馆的原址上,一座现代化大厦正在崛起。据说建成以后叫文化中心,图书馆、文化馆、档案馆等文化口的单位都搬里边去,里边还有剧场呢。
图书馆往南就是区委、区政府的大楼了。文章开头提到的邻居王叔叔的单位就在这里,我经常和王叔叔家的孩子到这里玩,只不过那会儿还是旧楼,新楼在旧楼的南边,紧挨着。
后来我三舅在区政府上班了,我经常去找他,再后来没想到我还在这座楼里工作过一段时间。那是“非典”刚刚过去的时候,天坛饭店转让后大装修,员工都遣散回家只拿生活费。经推荐我来到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帮忙,在《百年崇文图鉴》编辑部做编务,编务就是配合编辑工作,查找资料和搜寻老照片。

在编辑部工作时深感自己文化浅薄,从那时起我对文史更加充满了兴趣,在编辑部里结识了许多老师都让我受益匪浅,尤其是在这里结识被誉为“北京民间活字典”的王永斌老先生,王老的睿智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敬仰。
出政府大楼往南就是崇文分局和出入境接待大厅了,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关闭好多年了。再往南就是当时幸福大街上最有名的大饭庄——同春楼,现在原地儿是便宜坊烤鸭店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饭店的同事在这儿办的婚礼。为什么在这儿办婚礼呢,因为另外一位同事的舅舅是这儿的厨师长,熟人好办事哈。新郎是饭店的厨师,新娘是服务员,那会儿饭店里厨师找服务员很普遍。那天婚礼挺热闹,好多同事都去了。
同春楼再往南就是幸福百货商场了,小时候没去过什么大商场,觉得这里就不小,现在商场的一部分是物美超市。幸福百货商场在福光路的西口路北,福光路东西走向,可蜿蜒到达光明楼。幸福小学就在这条路上,合并后,现在是光明小学。福光路把一片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居民楼分成了幸福南里和北里。
当年我的一位朋友就在此居住,小两口新婚燕尔,和别人合住在两居室里。合住是那个年代的产物,这一般都是单位的房,粥少僧多,一套单元楼两家合住,共用厨房和厕所,要多不方便有多不方便,那次去朋友家串门我真是长了见识。
到了朋友家才知道,朋友家和另一家还真是关系不好,这谁也不怪,只能怪这种奇特的居住方式。那厨房进去感觉如同进了洞穴,墙上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,水管子上的油泥已经开始滴落,两家儿的油盐酱醋都锁着。
朋友小两口还要请我吃饭,我们一起在房间内把菜择好,朋友像特务一样出房间打探,确定那家儿已经做完饭了,朋友临出房间时的一个动作让我大大大大大……地吃惊,他把一个灯泡揣进了兜里。妈耶!原来灯泡两家都各用各的,您说这房住的要多憋屈有多憋屈。
崇文三幼也在幸福北里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三幼就和台湾的一家幼教机构合作,开创了幼教办园的新理念。那会儿入园可费劲了,得到处托人弄戗,估计现在情况也好不了多少。
在这福光路上也有几家饭馆——东北菜、大妈家常菜、程记肉饼店。这其中除了大妈家常菜关门以外,其他两家还在营业,程记肉饼店的伙计现在成了老板。
福光路的西口路南是时源涮肉,这里也卖烤肉,肉好,口味佳,因为这里的厨师长以前是国安宾馆烧烤厅的厨师,此人姓马。后来时源涮肉搬到夕照寺去了。
过了时源涮肉又是幸福大街上的大单位——崇文区工人俱乐部,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看电影。1988年翻建后改名为崇文区工人文化宫,这里有台球厅、布达拉歌舞世界(一说还有龙宫舞厅、红太阳歌厅,我那会儿还小,这些地方没去过)、乒乓球厅、游艺厅等设施,当时是饭店员工经常玩耍的地方。
当然这里还有电影院,那会儿饭店工会净发这儿的电影票,可没少在这儿看电影,饭店还在剧场开过联欢会。
文化宫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引进资金,先后建立了田园酒家、裕禾纺织品部、竹子发屋、地毯展销厅等。
现在的文化宫又称红剧场,每天都上映一部叫《功夫传奇》的舞台剧。此剧将武术、硬气功、舞蹈、杂技、魔术等艺术表演形式及数字多媒体技术兼容并蓄,以感情丰富的故事表达功夫的真谛。
观看此剧的多为外国游客,每晚拉外宾的大轿子车都把幸福大街南口附近弄得异常热闹。
文化宫再往南有饭馆、发屋、建行营业厅、修车摊等。
汇友涮肉以前就在街面儿上,后来拓宽马路,汇友搬到了东边楼房的一层。在这一段还有一家特别神奇的饭馆,这家饭馆叫什么已经忘了,因为这家儿有一名女服务员叫扬子,大家都管这家饭馆叫扬子了。这饭馆面积不大,就是两间临街的平房,里外屋儿。可当年这里可是体育界名宿们常聚会之地。
我当时特别纳闷——大不的店堂,几乎没有任何装修,饭菜虽也不错,但也没什么惊人之处,这儿怎么就能招来体育名人呢。还得说扬子这姑娘,扬子人长得不算漂亮但十分耐看,服务态度极好,人勤快会说话,关键还会来事儿。一来二去运动员成了这里的常客,慢慢的就变成他们的聚点了,当时在这看见大双、小双是常有的事儿。
扬子饭馆再往南有一家理发馆,当年的新潮理发馆都叫发屋,这家叫九〇发屋。据说这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歌星韩军开的,韩军和李晓东当年合作了三盘磁带,名字都叫《星座》,他俩已翻唱为主,学谁像谁,他俩从没在电视或晚会上出现过,相当神秘。说是韩军开的九〇发屋,我看比较靠谱,因为在《星座》专辑的歌片上印有“发型:九〇发屋”的字样,反正这发屋和他俩有关系。
把着幸福大街南口路东,马路边上是一修车摊儿。那会儿骑自行车的人多,修车的生意特别好。老去那儿修车,和修车师傅也是半熟脸儿,有一次去修车,正好饭店日餐厨房的马厨师也在那儿。我当年和修车师傅的一段对话马厨师至今还记得,他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。
话说那天修车师傅和我聊天,问我穿的运动鞋多少钱。我较早就写过 我和运动鞋的故事,也许因为打小离体育馆路比较近,一直喜欢穿运动鞋,上了班就更讲究了,那天我穿得是一双耐克的皮面运动鞋。
跟修车师傅说的这鞋多少钱我忘了,反正这鞋在当时不便宜。修车师傅的答话很精彩——(京骂口头语略过),买头牛才多少钱啊!
现在大家看到的幸福大街是本世纪初改造的,改造后的幸福大街拓宽至40米。
文章的最后说说幸福南里12号楼吧。12号楼就在幸福大街南口路东,每年国庆节都在这楼下布置花坛。
以前从12号楼下经过时我都有这样的想法——这栋楼肯定不简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这楼从外面就能看出每层的挑高超过一般的居民楼,而且窗子很大。
自从认识了莫阿姨我才把12号楼的谜团解开。先说说怎么认识这位莫阿姨的吧。以前我写过《今天和老街坊们聊聊体育馆路》这篇文章,莫阿姨从北京体育馆诞生的那个年代就在体委工作,她现在已是八十几岁的高龄,现移居海外。她是通过国内的朋友给她转发的我这篇文章才辗转联系上我的。
莫阿姨告诉我她那时就住在幸福南里12号楼,这楼当初盖的是举重运动员训练楼,所以墙体厚,房间高,抗震性能极好,这一栋楼有专用的锅炉房,后来盖了专门的举重房,这里就改成局长楼了。当时的局长是魏继统、曲治全等。

我自从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后,我先后认识了几位读者,有以前住在两广路的刘大哥、爱好收藏的孙先生、住在体育馆路的老邵、和老邵的朋友薛哥,以及在体委工作了一辈子、和体育馆路有极深感情的莫阿姨,还有和莫阿姨同样经历的同事加闺蜜杨阿姨。
有相同爱好的朋友越来越多,我们都爱回忆以前的事情,有人说爱回忆是衰老的表现,我不同意此观点。我觉得爱回忆是丰厚生活阅历的体现,爱回忆的人都热爱生活。
我觉得自己是念旧不恋旧的人,其实眼下的生活是最好的,科技给我们带来无限的便捷。我们之所以要写这些回忆的文章,是给后人留下反映前人生存状态乃至生命状态的一点痕迹。
在写这篇文章时经常在网上搜“幸福大街”这个词条,我才知道有一支摇滚乐队就叫幸福大街。这支乐队主唱是个女的,歌曲有点儿另类。
还搜着了另外一首歌,歌名就叫《幸福大街的四合院》
这歌词有点儿意思:
幸福大街的北巷口儿
有个四合院儿
刘大爷就住在
四合院儿的最里边儿
每天这一大清早儿
蹬着破三轮儿
满大街扯着嗓子叫卖
那苍蝇拍儿
转载请注明:玄武区聚富迈设计服务中心-集团电话交换机网 » 电话交换机 » 二红一白三部电话机(一红二白三黑指的是什么)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B5编程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